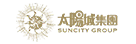专家呼吁:将“减负”方针融入教育监管考核机制 □ 本报记者 丁一 夜幕降临,伴随清脆的信息提示音,身处山东济南的王女士手机屏幕亮起——原来是就读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班级群里有了新通知,老师发送了一份需自行印制的数学专题练习——共计两页A4幅面,并要求隔日清晨上交。王女士立即拿起电动车钥匙,急忙下楼,直奔最近的文印店。 类似的情景,近年已在她家中反复出现。记者调查时了解到,许多家长与王女士有着相同体会,都曾遭遇深夜“紧急打印”的困扰,微信班级群里不时涌现的作业文件,已演变为众多家庭的日常“功课”。 这种打印作业的模式究竟为家长带来了何种实际压力?其深层又反映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症结?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对此进行了专题调查。 家庭印制作业:家长之重负 “每周平均需要印制三到五次作业,内容或是练习题,或是复习材料。”王女士向记者透露。 “有时因事务繁忙未能及时留意群消息,有时则是老师发布打印作业的时间较晚,导致无法及时为孩子完成打印,因为店铺已经打烊。”王女士表示,这种“夜半寻印难”的困境,常使家中陷入焦头烂额与不安。 王女士曾尝试与教师沟通。“记得有一次,我向语文老师提及打印作业量大,得到的答复却是‘想做就打,不做也罢’。” 此类回应令王女士深感无奈。 宗女士家住山东枣庄,她的孩子目前就读初中二年级,同样承受着类似的困扰。 受访时,她向记者追忆孩子初一阶段的境况。“印制任务确实沉重,工作日每天需印两页,周末则多达五六页。一个学期下来,我将孩子已完成的打印作业整理堆叠后测量,即使多数已上交老师,家中留存的练习纸仍堆叠近0.1米高。若据此推算,孩子一学期内印出的作业总量高度或将逾越0.2米。” “家中不设打印设备,每次印制都如同在执行一项紧急指令。”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如此形容。她直言,寻找文印店铺、来回奔波、排队等候,整个过程通常会耗去半小时甚至更多。 宗女士介绍称,印制作业内容多以语文、英语学科为主,通常是教师临时性布置的练习卷、备考资料或听写稿。尽管教师常提及“条件允许的家长可自行印制”,但绝大多数家长仍会选择打印,因某些作业内容(如函数图像、几何图形等)无法手抄,只能进行打印。 “这确实已成为我们家庭的一项负担。”王女士表示。首当其冲的是显性的经济支出,每次打印两三元,一学年累计下来便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 相较于经济层面的压力,精神上的负担更为沉重。对王女士而言,协助孩子印制作业已融入日常生活,及时关注班级群、课程群更是演变为一种“惯性”,这些都意味着时间与精力的持续付出。 尽管内心深感困扰,但普遍的家长群体选择了缄默。 “我从未向校方或教师提出印制作业过量的问题。”朱女士向记者坦言,主要顾虑在于,担心一旦反馈,教师可能认为家长“麻烦”,反而对孩子的学业或评价产生负面影响。 “倘若就打印作业数量过多一事提出异议,教师或许会认为家长不希望孩子完成作业。”宗女士表达了她的担忧。在“一切为孩子学业着想”的预设下,任何对作业布置的疑问都可能被误读为“不配合”学校的教学安排,进而可能波及孩子的学习表现。 这份普遍的沉默,使得问题始终囿于家庭层面,难以获得校方的重视与实质性解决。 教学职责向家庭转移:家长成“隐形助教” 2021年7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,其中清晰要求全面缩减作业总量及所用时间。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,教师频繁通过微信群布置需由家长自行印制的作业,此举本身就与“双减”政策的初衷理念背道而驰。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姚金菊教授剖析称,过度仰赖家庭印制作业,实质是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链条的“末端执行者”,模糊了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职责界限。一方面,这规避了对学校作业总量的监督,导致学生作业负担“表面减轻实则增加”;另一方面,也加剧了家长负担,将原本应由学校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家庭。“双减”政策明确规定“教师需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,初中生在校内完成绝大部分书面作业”,家长职责在于引导孩子完成“少量书面作业”,而非充当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要角色。 “将家长印制作业演变为学生完成学业的强制性、常态化前置环节,其本质是将学校应履行的教学保障义务转移给了家长。”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阐述道。 她指出,此现象映照出当前教育体系中的深层冲突,即家庭与学校协同育人责任边界的模糊化。诸如印制作业等原本由教师履行的教学管理职能被转移给家长,使得家校共育异化为“家庭代教”,家长甚至被迫扮演“校外教师”的角色。 刘一玮分析,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的偏差与政策本身的稳定性不足。 “‘双减’政策的初衷旨在促使学校与教师提升作业品质、科学调控总量,但要求家长自行印制作业,这无疑是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一种变异。此外,‘双减’政策作为一项行政规范性文件,其法律效力与稳定性本质上仍低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。”她补充道。 在姚金菊教授看来,“双减”政策在落地实施中遭遇两大难题:其一,政策与现有法律法规的接轨存在不足,尽管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载有保障休息权的条款,《教育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亦有确保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,但“双减”政策与这些上位法缺乏有效衔接;其二,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力量和监管技术相对匮乏,这使得学校或教师得以通过相对“不显眼”的手段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督,从而导致对“双减”政策执行情况的常态化监管难以有效开展。 违规作业布置:必须追责 专家们普遍认为,要有效解决此类问题,必须将教育减负工作纳入法治化框架。 姚金菊教授指出,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教育法》及《义务教育法》中有关教育减负的条款,构成了“双减”法治化的基石;应借由部门规章等形式引导学校推进“减负”工作的制度化建设,使“双减”政策真正转化为学校的内部规章;在具体实施层面,则应强化教育评估与监管力度,并可考虑将其纳入教育督导考核体系。 “亟需依法厘清教育活动中各参与主体的法律权责。要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强度,配备充足的专职执法人员,对违规要求家长印制作业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。并健全问责机制,对于那些违规布置印制作业、变相加重学生负担的学校,应依法施以通报批评、削减经费等惩戒。”刘一玮强调。 姚金菊倡议,教育本应回归其核心使命:服务学生的全面成长。她指出,教学革新与减负政策应协同并进,通过提升教学品质、深化教学研究、构建高效课堂,确保学生能在校内掌握绝大部分知识;同时,要多元化学生评价模式,允许教师在现有资源库或备案通过后,灵活选用、组合或微调补充习题,使课外练习更具“正当性”。在严格遵循“总量控制”原则的基础上,还应进一步对各类作业(如预习性、巩固性、探究性、阅读性作业)提出具体比例指导意见。 刘一玮提议构建共享型作业资源库。着手开发高质量的基础性与拓展性作业,丰富不同难度层次的作业形式,例如探究式任务等;并大力推广线上作业平台,以实现分层教学、弹性布置及个性化推送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的压力,并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。 “教师应考虑通过学校统一印制或集中订购习题册等途径,由学校教研部门负责完成,以杜绝将此项事务转嫁给家长和学生个人。同时,必须明确作业发布渠道与规范格式,通过官方指定的教学平台进行统一发布;若需提供电子版资料,务必提前整合打包、一次性提供,严禁零散、突发性的群消息轰炸。”姚金菊补充说。